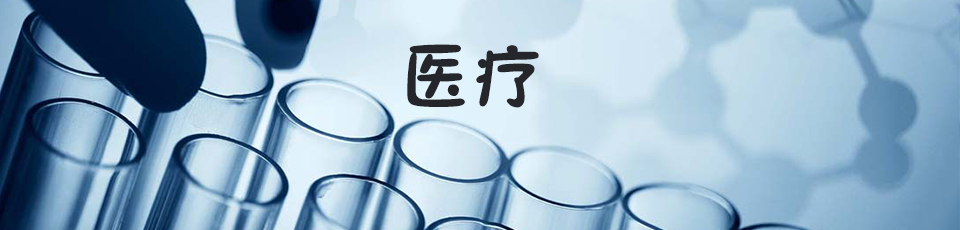大唐雷音寺
日前参加了《健康时报》主办的中美医疗交流活动,针对中国孩子的国际医疗救助,医院开始在中国拓展市场,还和盛诺一家签署了合建诊疗中心的协议。
在交流活动现场,有这样一场中美医生关于行业、关于尊严的一场对话。
参与对话的有:医院院长、国际业务拓展总监罗伯特·舒曼,医院神经内科神经调控项目主任、哈佛大学医学院副教授亚历山大·罗滕伯格,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哈佛大学医学院副教授A.K.卡泽博士。国内的专医院儿科及儿科癫痫中心主任姜玉武教授;首都医医院儿童心脏内科副主任丁文虹教授。
姜玉武:其实儿科医生是整个中国医疗行业不景气的缩影。做一个简单的对比,我在中国是一个科主任,我跟A.K.卡泽医生收入的差别不是1、2倍的问题了。当一个人生活的有尊严才能更好的为其他人服务,但首先我们是普通人,也是上有老下有小。
所以,解决儿科医生荒的问题,首先是让医生有一个体面的生活,这是最根本的一条。现在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长期积累下来的体制的问题,导致了现在儿科医生的收入是非常不尽如人意,至少在整个社会上还达不到中上的水平。但是儿科医生的付出,与承担的风险和劳动强度不成正比,因为儿科医生面对的是“哑病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给一个成人病人取血他可以老老实实待在那里不动,但是婴儿取血至少2个护士、1个家长来操作,但是收费是一模一样的。支出成本高,劳动力成本也高,但是获得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非常的不合理。
医院医院,医院应该是政府负责主要支出,但医院大部分支出是自己挣出来的,医院的科室里注定不是一个有好收入的科室,整体工资偏低。
儿科受培训的机会,包括各个方面的支持,包括做科研经费的支持等等,都比成人科要少。一个人要获得成就感,除了收入以外,还有受尊重的程度。中国人常开玩笑说的话“小儿科”,其实就是一个贬义词。如果整个社会对于儿科医生缺乏尊重的话,他们就不可能有很好的职业成就感,也就没人愿意做,来了也留不住。
包括培训的机会,咱们国家现在医改有一个问题,医改对硬件投入多,但是对于人的投入相对不足。比如医院医院还好,设备甚至某些方面比我们要求还高,都是最好的仪器,但是医生可能连仪器都不会用,医院仪器都没有开封。因为楼是容易看得见的,见成效快,县医院建的高楼很漂亮,但是对基层医生、护士等人的投入很少。除了政府投入的培训,其他企业对于培训的支持,儿科也比成人少,可以看到成人医生开会的规模和档次都比儿科高,儿科医生接受培训的机会就比较少,上升空间也小。
类似的还有急诊科、精神科,都是相对比较弱势的科室,因为这些科室都不是收入比较高的、受重视程度高的科室,所以发展就不好。所以首先要改变一个理念,医院。医院里儿科肯定不能背负创收的负担,让院长在院内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不公平的,比如妇产科创收那么多凭什么让人家补贴儿科。好的做法,应该是从医保等方面想办法,应该适当的提高儿科诊疗的收费,因为确实付出的劳动量大,多付的费用应该从医保报销上来补贴,增加的医疗收入应该用于补贴儿科医生和护士的收入,这样既不增加家庭的负担,同时也能够提高医生和护士的待遇。医院里把其他科的钱拿来补贴儿科,实际上这个效果并不理想,也是不尽合理的。
作为一个一线的医生我就是这样的感受,也是实话实说。当然我也没希望儿科收入特别高,即使在美国儿科医生的收入也不是特别高的,最起码也要维持中上的水平,让他衣食无忧,他才能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丁文虹:姜教授讲了很多现实的问题,稍微补充一点。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其实也有它的历史因素。因为我们国家有一个特殊的一孩政策,这么多年,那个时候小人口增加不是很多的时候,医院的儿科实际工作是不满的,没有那么多的儿童病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因为涉及到自负盈亏的问题,这些科室不挣钱,甚至在我刚上班,九几年的时候,我们的科室6月份、7月份几乎一个月只有几个病人,全院的科室都说把儿科关掉,好像是我们没有生存的必要了。这些年造成了一些院校比如儿科专业的萎缩,培养一个医生需要多少年,就像砍树不再栽了一样,有多少年是荒的,突然想用这片林子一看还没有栽树。这就是现实问题,儿科医生确实少。
一孩政策这么久了之后,全家围绕着这一个太阳,即使没有重病,医院来也非常焦虑,生活中所有的压力再加上一个孩子都要交给医生解决,对医生来说也有精神上的压力,包括儿科的医护。他不仅要面对一个病人,还要面对整个家庭的情绪,所以压力也是很大的。
儿科医生的收入低是毋庸置疑的,作为一个儿科医生,想能够一直坚持干下去,其实还有一份对这个专业的爱,真的是舍不得。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努力,还可以放弃一些利益,再累还可以坚持。我想鼓励年轻人能够接上来再做儿科医生的动力,像姜教授说的,工作上有一个上进的动力,有可以学到的东西,可以进步,生活上有基本的保障,社会上有足够的尊重。这些都加起来,我们的儿科也应该还是可以兴旺发达的。而且“二孩”放开了,其实我们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开始,如果国家能给一定的政策,社会能给一定的尊重,我们的儿科医生和国外的高级同行能够增加交流,能够提高整体队伍的水平以及对下一代的服务能够做到更上档次,能够真正满足人民的需要,还是会受到大家的尊重和欢迎的。
A.K.卡泽:在美国也发生过类似的危机,我们对初级医生也是极度的缺乏,在一段时间内。政府做了很大的投资,鼓励年轻人做全科医生,提高报销率,有一些医学院专门开设这样的项目培养全科医生。政府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来改善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应该可以做出相应的努力。
姜玉武:现在有一种观点,我们要解决儿科医生荒,要重新开设儿科系,我不认为这是应急的好办法。因为真正的儿科医生培养出来,就算五年的医学院加上三年的规培,一个医生要能够用得上至少八年,重新开儿科系八年后第一批学生才能出来,这段时间怎么办,八年抗战吗?!实际上中国的医疗资源没有很好的被利用。比如我,作为一个神经科专家至少需要20年的培训才能达到这个水平。跟我同水平的医生在医院儿科还要看感冒发烧,拉肚子也得看,这些常见疾病,合格的住院医师就可以处理,因此实际上是培养了20年的医生当培养3年的医生来用,是不是资源浪费?!。反过来,家长肯定不是这样想的,即使我得了一个感冒我也要找姜玉武主任看,这样才体现我的价值,我的孩子宝贝。但是作为一个卫生行业的领导者不能这样想,应该针对全国的老百姓来想,实际上就是分级诊疗的概念,还是应该尽快的推动分级诊疗,这是能够真正短期内缓解儿科医疗或其他医疗困境的办法。提高利用率才是最好的,增加医生的培养,八年后才能见到,这种办法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一是要充分挖掘现有医疗资源的作用,二是要留住人。大量的人才不断流失,因为压力太大,收入太低,都是高知识人群,他完全可以不做医生。这两条如果能够重新的利用,吸引住、留住人可以很快的改观,是可以很快见效的。
主持人:请问三位美国专家,我听到一个说法,美国为了保证医生的高收入,对医生的数量采取了限制措施,每年新增的医生3万左右,以确保这个阶层的收入达到一定的高度,是不是这样。
罗伯特·舒曼:当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市场是公开的。我们自己的儿科医生也不够,我们很珍惜儿科医生,因为他们会照顾孩子。我们很强调预防性,在疾病没有出现症状之前就及时的进行预警。比如肥胖、肺部疾病,这样能够保证小孩顺利的成长,能够享受到好的生活质量。
亚历山大·罗滕伯格:美国医生每一个人看的病人是很少的,一个上午就看4个病人,像我是看的慢的,一个上午看15个病人,医院一个上午看50个病人,你就没有时间做创新和研究。美国的体系虽然医生看似很多,实际上有大量的医生是做研究和创新的,所以弹性比较好。每一个医生只是一部分时间在做临床医疗,医院医院,医院是国家级的,但是比他们的时间少得多。我在美国等待过两年,他们有相当多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科研,研究复杂的病例,所以病人的感受也可以很好。在中国一个病人只能看几分钟,所以两头不讨好,大夫想好好看,但是政府又规定必须看这么多病人。
主持人:两位专家每年整个工作时间用于科研的时间有多少,刚才姜教授称亚历山大·罗滕伯格是临床科学家,临床科研是基于什么,医院对你们有没有发表论文数量的要求,或者每年必须完成多少论文,今年比去年要多发几篇论文,是基于什么标准做科研。还有胶水的发明,发明者是不是在经济上也有很大的受益。
亚历山大·罗滕伯格:我们做研究是出于自愿的,因为真的很想患者解决问题,我们的研究是为了找出新的解决办法,在临床上要进行一些试验找出新的解决办法。1/3的时间用于临床,2/3的时间用于科研。
A.K.卡泽:我很同意亚历山大·罗滕伯格医生的观点,我们都是出于自愿进行研究的。比如临床我们发现问题,就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行试验研究新的办法。医院在招人的时候本身就要招一些愿意为科学奉献的人,我大部分时间用于科研,一部分时间用于临床。
在医院把科研的成果商业化是有一定流程的,作为发明人本身是会有一定比例的经济上的受益,但是作为Nido医生的同事,我很了解他,他做这个并不是为了经济上的受益。
主持人:刚才既然提到说我们招的人就是热爱科学、热爱研究的人,从美国专家开始,请四位回答一下,你们当初报考医学院是出于对于医学的热爱,还是父母要求你们填这个志愿的。在报考医学院之前,你们有没有做过医疗助理这样社会服务的工作。
A.K.卡泽:因为我是出生于医生世家,家庭中有很多医生,我有很多的模范可以效仿,这就是我之所以选择当医生的原则。
亚历山大·罗滕伯格:我的家庭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医生,之前也没有接触过任何医疗相关的东西,但是很自然的我就选择了当医生。
丁文虹:我只能说实话了,我爸爸是医生,其实我并不想当医生,是我爸爸我妈妈让我当医生,说你看你爸爸一屋子书,你不接班这些书怎么办。如果从事医学行业,混日子也还行,如果非常的投入,想做一件事情对于女同志来说非常难因为社会认可女性在家里占主导地位,应该相夫教子,如果医院,家庭肯定就会被忽略。我这个人一进到医学行业,学上医以后我就觉得我不能回头了,我觉得我是螺丝钉,后来成为了一种惯性。到这么多年我爱上了儿科行业,很喜欢为孩子看病。
姜玉武:我也实话实说我也是被父母逼着学医的,我不是医学世家,我们家从来没有医生,我也不像亚历山大·罗滕伯格从小就喜欢医学,我是上大学之后逐渐喜欢医生的。我是北医毕业的,跟老师交流的很好,使我越来越对医学感兴趣。当时我上学是六年制的,三年在基础部还没有什么特殊感觉,但是一接触病人以后就特别喜欢医生这个行业。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你高于动物的那部分,你能够帮助到别人,你能够为社会做出很多贡献,医生确实是最接近于神的一种职业,因为你手里握着生命。
我总是跟我的学生说,医生属于良心活,所以我也不认为你把医生打了、砍了、杀了他们就好好干活了,他们好好干是发自内心的,绝不是逼得出来的,一定是他内心喜欢这个职业。我们绝大部分的医生是内心喜欢,想帮助病人。我老是跟病人说把你治坏了对我有什么好处,把你治好了我又得名又得利吧,我把你治坏了,我图什么?!所以,我觉得人心的本意是善良的,为什么有一些中国的医生做出一些老百姓不满意的事情,你想中国医生可以为几十块钱拿回扣,让美国的同行听到他们会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应该觉得脸红,但是我们社会应该感到脸红,因为这就是丧失尊严、不要脸了。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很痛苦的,为了几十块钱拿这个回扣。
我看到报纸原来有一个关于报纸的回扣,某某医生拿了块钱,我有想哭的感觉。医生为了块钱去做这种很可耻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人性是一样的,不要觉得中国的医生就不爱病人,中国的医生就不好,美国的医生就好。实际上我们也热爱这个行业,我们也愿意做科研,只是说我们的医疗体制也好,或者说设计是不是给他这种机会,让他做一个高尚的人,让他做一个也喜欢发明、也喜欢创造的人。如果是一个医生犯这种错误,可能是个人问题,如果大量医生犯这种错误,那一定是制度的问题,不是医生的问题。虽然很多医生抱怨,但是我认识的这些医生他们除了做好医生,一样也都是发自内心的在做科研,我们也热爱我们的科研工作,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都是被逼无奈做的科研,我们跟他们美国医生没有区别的,只是说能给我们的机会和空间太少了。他们可以70%的时间做科研,医院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我们应该共同的努力,给中国的医学和中国的医生更多宽松的空间,我们一定会做的与他们一样好。
今天的彩蛋:《沙弥的筋骨》第九段连载藏在这里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xibuniuzaiku.com/ylfl/3272.html